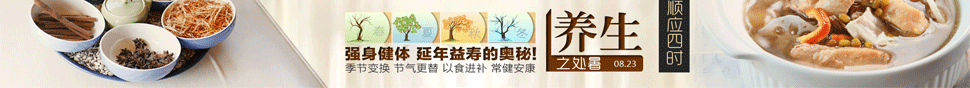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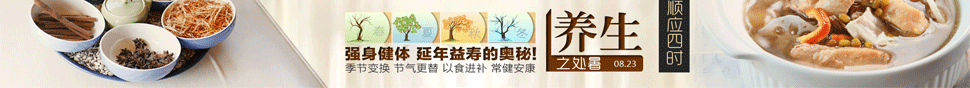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最近我与文学群的晚辈朱二哥以及收藏古玩家龙老师,因文学而结缘,多次交流起来。那个周六,我们三人又组了个局,约上来自省城的杜鹃老师,结伴到了江埔街高峰村下辖的杨村观鸡啼石。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来到高峰村的杨村。若没有朱二哥的热心带路,我又怎会遇见这一条鲜为人知的美丽乡村呢!
杨村果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地方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河一石,都有它的特色,映入眼帘的山乡风貌,让我喜出望外。原来,这里的村民就是宋朝的忠烈杨家将后代,他们的祖辈先是从中原南迁至新丰,然后在清朝乾隆年间继续南迁至鸡啼石后面山脚下,至今将近三百年,人口超过四百矣。村里一幢幢农村民居楼房拔地而起,楼房前是一大片混凝土水泥平地,约有平米。这里便是村里的晒谷场,俗称大禾堂了。禾堂前则是环绕着村前的半月形的古鱼塘,鱼塘外就是村民耕作的一大片农田。朱二哥说,这就是占地超过一千亩的鸡啼石农田了。鱼塘周边按装了褐红色的栏杆,靠楼房的一边栏杆旁种上各种各样的树木:白兰,柳树等,树影婆娑,与天上的白云,地上的楼房一起倒影在平静如镜的鱼塘水面上,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山水田园风光。我们就沿着崭新的混凝土机耕路去看鸡啼石。鸡啼石,朱二哥自诩是鸡啼石的代言人,每次跟新朋友介绍从化,介绍家乡,言必提起鸡啼石。鸡啼石是小海河畔的“怪石”,也成为杨村与大陂田村,两村村民心中的神石。我们边走边谈论村民种植的作物。突然,听到朱二哥说:“祥伯祥婶,原来你们在这里摘龙眼啊。”“是啊,过来吃龙眼吧!我种的龙眼特别甜!”祥婶热情地说。大概六分地,田地错落有致地种着十几棵龙眼树,树身已有六年以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看来俩老管理到位。我只见一位六十多岁头发几乎全白,鹅蛋脸,中等身材的妇人眉开眼笑地递给杜鹃老师一大串龙眼,自豪地说:“纯正的石荚龙眼,又大又甜,尝尝吧!”杜鹃老师接过龙眼说:“别客气!”祥婶又在龙眼树下修剪整理树下一堆龙眼,她把一串串的大龙眼有序地放进箩筐里。而在树上的祥伯麻利地剪摘龙眼,不一会儿又摘满筐了。祥伯的腰背有点驼,清瘦的脸庞布满皱纹,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散发着一股钢铁般神情。他是纤维厂(国企)退休工人,几个孩子成家在城里,退休后,俩老常回来耕作。祥伯累得坐在树下跟我们说话,祥婶开心地指着一畦长势旺盛的草丛说:“鱼腥草,清热解毒,还有黄肉姜.....”这时我仔细一看,祥婶这几分田地里除了种有龙眼树还有苦麦,番薯叶,茄子,鱼腥草,假莞茜等确是百宝,杨家的百草园。突然,我发现百草园种了一片小时候随处可见的"地胆头",一种遗失多年的药材,现成珍稀的物种。瞬间,我对眼前的百草园甚感兴趣。另一畦地上长着又长又尖的绿叶,经过祥婶的介绍,我认识这种"仙茅"的药材,土名"地棕",绿叶红头,广东人煲汤的材料,补肾补气血等多种作用,还见识了沙姜的样子,吃过沙姜却第一次见到它的生长。沙姜是一种佐料,去除腥味发挥最佳功效,常用于蒸鸡做鱼的配料。一个普通的田园有着不普通的耕种,一位平凡的村民有着不平凡的奋斗。祥伯耕种的百草园成为儿孙节假日回乡的乐园,守着一份亲近土地的亲情。我们继续去看鸡啼石,走在机耕路上,远远望见小海河,望见野草几乎掩盖了的鸡蹄石。走近鸡啼石,我们却不敢亲踏它。那一块块突兀嶙峋的岩石堆积形成"鸡啼"的形状。鸡啼石金鸡独立,孤零零地望着大陂田的人们。鸡啼石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杨村和大陂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许是它的功劳,许是它的精神,许是它的神奇,村民勤劳致富,安居乐业。鸡啼石与小海河相伴,山水无言,人间友爱。鸡啼石架起杨村与大陂田两岸的一座彩虹桥,村民沿着它的足迹一如既往地和睦共处。滨棻,文学爱好者,从化作协会员,散文作品见于从化本地报纸、杂志。
图文/编辑:滨棻,点亮“在看”呗????
邝艳芬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xianmaoa.com/xmyx/111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