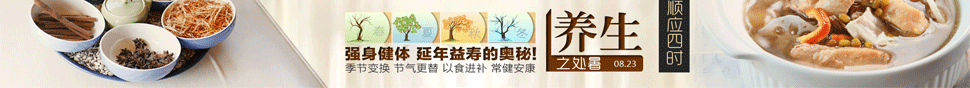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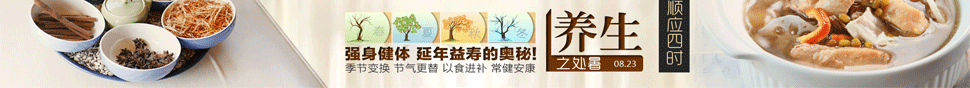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点击上方“岔路发布”发现更多精彩
三上冠峰
陈剑飞
文
年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推出了集系列纪录片《边疆行》,跨越9省区沿我国与14个国家的国境线,开展行程公里的实地拍摄,采编人员历经艰辛为国人撩起了神秘的边地风貌,也记下了祖国边疆特有的历史人文。生动而独特视角的记录片一经播出,以它的新奇与鲜有吸引住全国观众,收视率很高。看了这档节目,宁海广播电视台新闻敏感度很高的几个部室主任,马上策划了沿宁海邻县三门、天台、新昌、奉化、象山五县界域拍摄采风计划,并把栏目定名为《边界行》。看到这个计划后,我欣然同意,抽调广播与电视媒介有关人员组成了栏目组。第一站的拍摄路线是沿着王爱山岗采风。出于对这档新开栏目的重视与期待,我参与了第一天的拍摄行动,这也是我首次踏上王爱山岗。
以前多次带客人游浙东大峡谷,都是从白溪水库仰望王爱山岗,只见高峭的山上住着人家,炊烟升起与白云袅成一团。这些超然物外的岗上村庄,好像与天空更接近,和尘世渐远的另一个世界。这一次我是和栏目组奔着崭新的节目而去,采编人员对全新的节目方式都怀着一腔激情。实际上,我除了和记者一起参与过抗台报道外,也是难得和一线采编人员共同去完成一档节目。
我们在王爱山岗上的一处田野里,寻到了国务院设置的台州与宁波的界碑,找到了徐霞客曾经履步过的那段古道,找到了村里几位老人,听他们叙说发生在王爱山岗上的陈年旧事。
我们最后到达与新昌交界的一处山峰,听说对面山头即是新昌界,但对面山脚有一片山地还属于宁海,如果步行到那边,来回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我们在一处拉山货的缆车房里停下,看简陋的缆车缓缓地从山那边把收获的东西载过来,缆车从新昌那边的山,到达宁海这边的山,需要二十分钟时间。我们拍了运货缆车后,采访了几位山民和村干部,天色已不早,第一天的拍摄就可以满足三天的播出量。那天栏目组人员热情高涨,返程时都怀着一种莫名的兴奋。也许原来都是这个会议那个领导活动规定的采访程式,而这次是沿县域边界的随机采风,只有路线限制,没有主题限定,在寻找新闻线索上,采编人员都得到了充分的自主发挥。
王爱山岗西部山峦起伏,平均海拔米,最高为鸡冠尖(旧志作桐柏山)海拔米,因峰尖状如鸡冠,亦称冠峰。据明《崇祯宁海县志》载:“桐柏山,西四十里在天台极东宁海界上,相传葛玄炼丹宁和山中后徙此”。葛玄为葛洪从祖,是三国时道教灵宝派祖师。不管这“相传”是否可信,但这冠峰看来很不一般,和道仙之气有着那么一番的史载缘起。但那次《边界行》采风活动,我和冠峰擦肩而过。
我第一次真正上冠峰,是在老局长陈炳寿带领下去的,他曾担任过冠峰中学教导主任,和那片土地有着深深的感情。他约上几位好友,故地重游,也叫了我。当我爬上冠峰,一身大汗,回到冠峰中学旧址吃中饭时,早已饥肠辘辘,餐桌上尽是山货与肉类,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好吃的食物,新鲜爽口,大嚼了一顿。这可能和爬山的体能消耗太大,胃口大好有关吧。
第二次上冠峰,是与家人同行,当时巳经九十多岁的岳母也带上了。为照顾岳母年迈的身体,我们没走多远,只在冠峰中学附近悠转,吸吸清新的空气,看看辽阔的天空,采几处藓苔回家,把它敷在道地的花盆上。至今这些山地上的藓苔都爬起来了,在铁树身上延伸。一经下雨,这些翠绿的生命会复苏,可能在它们的记忆中,冠峰这块母地就是这般的潮湿与充满活力。
第三次上冠峰是因一幅照片而起。当我看到王剑波兄的“大河奔流工作室”公号里贴有“从冠峰看天台华顶山”一张风光照,从一片茶园向远处瞭望,华顶山上的建筑依稀可见。这个角度是前两次没看到的。我五次上华顶山,每次都和云锦杜鹃擦肩而过。在元明时期,我的祖上居天台射圃,至今我们每年都会去天台祭祖。但云锦杜鹃好像故意为难我似的,爬上华顶不是未绽或巳谢,没看到它满头披红,华锦一片的样子。我在想,是不是祖先故意让我多来几次祖籍地呢?还是我游子归乡的心不够虔诚呢?
从冠峰可以远眺天台最高峰华顶,从出生地宁海看到对面充满传说与灵气的天台祖籍地,何不是一件快事。怀着这般期待,应宁波一批文友相约,在今年3月23日再游冠峰。这回幸有曾在冠峰中学读书的王剑波和郑英明两位伴游。郑英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冠峰中学长住七年,对这片土地有着太深的感情与记忆,对这片山头每个角落都稔熟得能够背诵一样。一到冠峰,停下车,郑英明就当起地陪,就像踏上“七年之痒”电影中那片诱惑的土地一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是的,那青葱岁月的七年,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刻,在他人生中一定有满满的往事,诱发美好回忆,也乐于让我们在此刻此地分享。
有了他的引导,我再爬仰天湖。椭圆形的湖并不大,绕走一圈不过三五百步。山顶上一般罕见有湖。现在的季节湖水已干涸,长满了泛黄茅草,但湖边小溪仍然流水淙淙,有些凉意的水清澈见底。我情不自禁撩起水来,净了净双手。一般游客爬到仰天湖就算到了冠峰的最终景点,拍照留影就返程了。而这次有郑导在,当然还要继续寻踪。
我把从冠峰远眺天台华顶的想法告诉了他,郑英明继续带领我们向峰头西侧走去,这是一条鲜有人行走的旧路,棘草丛生,只隐约看见山路影子。在仰天湖尽头处,我拍了几张照片,匆忙跟上。终于在鸡冠尖的西侧看到了华顶山小馍头一样的山形。没带长焦镜头,只得用24—70的镜头拉了几张,又用手机拍了几张,幸好是苹果11,有变焦功能,还算过了瘾。华顶山上的建筑依然清晰,那片牵肠挂肚的云锦杜鹃呢?我想应该还未到绽放的时候。但今年暖春,谁知道她们有没有提前盛开呢?在向往华顶的一片眷念中,我们绕走山头一周,最终回到冠峰中学旧址。
想当年冠峰中学这些学子是怎样的辛苦求学,他们要爬六七十里山路,从早晨七点钟出发,下午四点才能到达学校。这一天的跋涉都是为了求知上学。听说他们班有一个女同学,从岔路来,当过白溪(水母溪)时,正值山洪暴发,经过溪上石墩时,不幸被洪水卷走。一个豆寇年华的学生,她的生命在求学之路上戛然而止。上学之路如此不易,要付出鲜活生命的代价;人生之路更不易,要做到善始善终需要和命运掰手腕。强者自强,这些同学有的踏上仕途,有的在各自岗位上拼搏一生,现在都到了退休年龄。世事恍惚,这个冠峰中学就是学子们梦一般的存在,也是他们人生路程上一个美好的驿站。正如王剑波在《我的青春跋涉在王爱山岗》文章里所说的:“这条山岗是我青春岁月的一段驿路,坡道上曾经闪动着我和我的同伴奋力跋涉的身影;这条山岗又像我人生之路的一座计程碑,和那些秀竹茂林、风声雨雾一起,镌刻在我的记忆里。”“一次次往返王爱山岗,一次次攀越冠峰山岭,我在那个年代的这段经历,也许是一种磨难,但同时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是这座大山给了我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
我从十年前第一次踏上王爱山岗,到这次三上冠峰,颇有几多感慨。当年求学的路是这么崎岖,学子们用脚板一步步踏上来,担着半月的米粮和腌菜,扛着一肩求知的期望。这是一条通向未来又转回老家的路。如今,“徐霞客游踪标志地”正在如火如荼展开,这条王爱山岗就是当年徐霞客游记开篇中,有着多处驻歇地记载的游途。想想明朝有这么一个奇人,搜遍天下山水,竟然挑选从这里开始下笔,幸哉冠峰!幸哉王爱山岗!
作者简介
陈剑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市县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作协理事,退休前为新闻媒体负责人。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已出版诗集多种。近期诗文兼顾,多篇关于摄影、美术和建筑的评论颇受好评。
□撰稿:陈剑飞
□编辑:归一
□审核:华庭天籁
·END·
岔路发布长按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