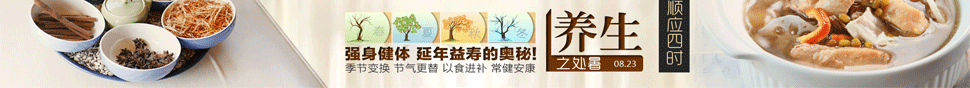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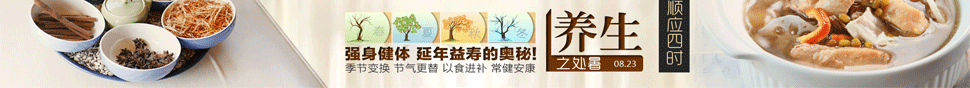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创作主题
作家吴念真曾说过:“记得你们、记得那些事,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这一切都已成了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请以“生命的刻痕”为主题,写一篇记叙文。
创作要求
1.以自己亲历的几个真实事件为基础,呈现事件的细节。
2.突出自己的特质,表现自我的心路转变历程。
3.运用富有创意的艺术手法,体现创新性表达。
4.字数在字以内。
5.题目自拟。
作品展示
《叶儿粑》
高二13班王梓萱
下过雨的山路总是难走。崎岖的山峰之间,仅有的那一条小土路变得湿滑泥泞。还没散去的晨雾模糊了道上人的视线,整座山峦隐在这面纱之后。清晨五点的朝阳还不足以穿透这层障壁,于是一切生灵像是褪了一层色。
就是在这样一个早上我第一次上山采叶子。做叶儿粑的叶子很奇特,我起初并不知道它叫什么,还以为是芭蕉。直到那天真的随奶奶亲自上山去采叶子我才知道那是四川乐山本地特有的大叶仙茅。在路上走了约十分钟我们就找到了这种大叶仙茅。我笨拙地把它长长的椭圆状叶片从根部掐断,一溜烟跑下山,跟家里人高声炫耀我的战利品。后来的三天我也一刻没闲,踮着脚把包着馅煮好的叶儿粑放到阳台上晾。剥开叶片咬开糯米尝到红豆沙的时候,那家乡的味道留在了我的胃里,也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但是,我自认不是个怀乡的人。到了北京后,我好像很快就在车水马龙间忘记了家乡的模样。由于我只会听乐山话而不会说,为了避免尴尬,我甚至有时跟不熟的人自称是北京人。
唯一跟家乡的联系,就是每天春节和土鸡腊肠一起寄来的叶儿粑。刚开始还觉得怀念,但架不住奶奶热情,一年寄一次,一次吃一年。尤其是在学校附近这个出门就能吃到山南海北美食的地方,家里成山的叶儿粑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直到有一年实在是吃不动,我和奶奶通了个电话委婉地要求她春节别寄叶儿粑了。谁想第二年春节又收了一山的叶儿粑,还包含了好多新口味,甜口咸口肉馅水果馅的一应俱全。电话那头奶奶说是我不爱吃原来的于是给我包了很多其他风味的。一个电话未完又收到十几张照片,一筐筐竹笼里叠放着比后山还搞得叶儿粑。我连忙用戴牙套不能吃粘牙的糯米搪塞才逃过一劫。看着这些快递箱,我纠结了一会儿,无奈之下还是都把它们扔掉了。
之后几年春节的快递里都没有那一箱满是大叶仙茅包着的叶儿粑了。久而久之,那糯米裹着红豆沙的香甜也只是我记忆深处虚无缥缈的一个象征罢了。
“这叶子好小啊,怎么包得住呢?”我不禁对眼前餐馆里的叶儿粑疑惑。“川菜馆都是这样的吧,不正宗吗?”朋友把小小的方形叶片撕开,没抬头地说。”“正宗乐山叶儿粑不是这么做的。叶子要用长圆形的大叶仙茅。”“你都多少年没吃了,说不定都改进了呢。”我一愣。是啊,多久没吃到奶奶包的叶儿粑了呢?她还需要每天清晨爬山摘新鲜的大叶仙茅吗?每年春节还吃叶儿粑吗?还用红豆沙当馅儿吗?
……多久没回家了呢?
于是,某年除夕,乐山。一个人高马大的女中学生追逐着一只野鸡奔跑在后山崎岖的田埂上。昨天夜里估计下了点雨,她最喜欢的白色运动鞋都被泥路染脏。但她好像不在意,挽起裤脚继续猛追。从山南追到山北,从山脚追到山顶,追到太阳从她正上方落到远处的桃树枝上挂住了,在这一刻她好像变了。或者说是,变回了她从前的、熟悉的那样。她以为她都忘了。但当她再站在这里时,她发现,这里的一切是如此亲切。因为这里,这里的山,这里的人,早已融入她的血液中。无论过了多久,这里一直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不可擦除,无可替代,像金属上的一道刻痕。即使在这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这道刻痕,名为家乡的刻痕,也不会消逝。
她最后还是没跑过那只鸡。推开门,空手而归的她抱歉地耸了耸肩:“抱歉了奶奶,今晚没鸡吃了。”她口中的奶奶笑着扔给她一包大叶仙茅:“莫得事。吃叶儿粑不?红豆沙馅儿的。”
《牙》
高二14班潘孟茜
我刚关掉和弟弟的视频聊天,就在最后一眼看到他动态的图像时意识到,他的牙齿已经长齐。从他搬到另一个城市读二年级到现在已经两年了,那时即使他最开心的笑容中也只有几颗小小的牙齿。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是家里最年长的孩子,更确切地说,更年长。我弟弟比我晚六年拥抱这个世界。他出生几个月后,我在离家很远的寄宿学校读一年级,几乎没有时间去见证他的成长,但这并没有导致我们几乎没有互动。
除了我教他唱歌、教他把纸片折成可爱的形状这些和睦相处的时候,每周五晚上放学回家,我和弟弟之间会发生单方面的争吵。以前我很喜欢毛绒玩具,所以每个星期天上学前,我都会收集玩具,把它们按一定的样式堆放起来。然而,它们总是被移走,甚至被错误地放在房子的一些不知名的角落,这显然是我的小弟弟做的。我大发雷霆,让他按照我组织的方式把它们放回去,但他似乎太天真而无法理解。这样的情况重复了几周、几个月或几年,我几乎记不清了。我父母把我的愤怒归因于他们所猜测的——我过于自私而不愿意去“分享”。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样。
几年过去了,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心态。作为一个从小远离家庭的孩子,尽管我一直认识到自己足够勇敢和独立,但我对毛绒玩具不同寻常的喜爱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安慰,以解决我一直未能抓住的安全感不足的问题。我的潜意识把每个周末都理想化为平日里的临时家庭团聚,然后驱使我期望“回家时一切都一样”,以弥补“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割裂感。那是我在寄宿学校上学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也是我弟弟平时的行为(实话说,在玩具上捣乱对孩子来说是很常见的)所加强的。虽然只要我和另一个体同住一个家,回家后事情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我只是固守这种思维方式,不太愿意去接受。
这种生活阶段性的割裂感导致了我在小学期间每周五的愤怒,并影响了我形成冷淡的性格。因为情绪的发泄没有用,我才逐渐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感,这让我觉得远离那些变化的事物和远离周围的人。我似乎不再在意自己的东西乱七八糟,也不再在意别人对我的态度比起以前怎么样。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曾过于理想化地对事物抱有太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反映于强烈的愤怒和极端的热情。实际上没有什么能与时间的流逝背道而驰,故而我的激情似乎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事情。我长大后出落成冷漠的性情,这与独立是不同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开始了一个新项目,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弟弟和他一起去了。我时不时会想起我的弟弟,他现在正处于牙齿过渡期的末期。
随着我逐渐长大,乳牙会逐渐脱落。每当我失去一个,它留下的空缺很快就会被一颗新生的恒牙填满,这颗牙更坚硬,更适合我们应付将来更难啃的东西。同样,几年前我对我弟弟孩提时代的天性产生的愤怒,只是一颗乳牙扎在我尚未成熟的牙龈上,而它现在已经无迹可寻。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在咀嚼时都不会想起那些丢失的乳牙。
《生命的刻痕》
高二15班李盈润
前一刻,我还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篝火旁噼啪烧灼的棉花糖夹饼干而垂涎;下一秒,我坐在空荡荡的隔离房间中,在纸上写下这一行字迹。前一天我们还为“在亚利桑那竟然也能买到纯正的大白兔奶糖”而雀跃不已;此时此刻,杂乱无章的元素充斥着周围的空间:干燥的鼻黏膜,尽力压制住胃里的呕吐感,发动机的嗡嗡声,令人毫无食欲的飞机餐饭菜气味,和怎么咽口水也打不通的咽鼓管。强烈的眩晕感随着口罩之下湿漉漉的空气一起被努力吞咽回肚肠。窗外已是夜色,飞机舷窗上映出了我发呆的样子。啊,真的好黑啊,什么也看不到啊。险些回不了家的我们,被末班飞机从流行病中救赎出来。可是返回故土的那一刻,又会是怎么样的图景呢?
酒精,白色和蓝色,消毒水。国内的光景似乎也不比大西洋彼岸优越,世界人民在例行的防疫琐事上也达成了共识。不同的是时间流逝之后的心态:我曾对口罩这件物品感到恐惧,毕竟我们无从知道它到底是一张坚实的保护伞,还是一层蒙在脸上的安慰剂。尽管如此,人们从不敢触碰覆在脸上的那层无纺布,它似乎成了封锁内心安全感的底线。
但回国后的隔离生活的单调性,为我的一切焦虑打了一剂麻醉针。我渐渐开始相信,有些问题的答案是无从知晓的;面对生命中无法规避的一些痕迹,只要把问题留给别人解决就好----我不是那个应该追溯问题本源的人。于是乎,我开始变得麻木,开始对周遭的事物置之不理。
直到我翻开了那本书的第一页。我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借来的那本《鼠疫》,封面是枯燥的牛皮纸黄色,红黑两色的书名触目惊心。可能是设计者还嫌不够惊悚吧,于是加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咀嚼着前言的文字。这时候妈妈推门而入,我想糟了,妈妈最讨厌我把图书馆的书拿到床上读了,嫌脏。我连忙坐了起来,又盯着封皮看了一会,好像看见了鼠疫耶尔森菌对数期增殖的景象。
于是我从第一章开始阅读。情节很朴素,讲的是一座名叫奥兰的城市被鼠疫侵袭,主人公里厄医生和伙伴一起抗疫的故事。不同于那些情节紧凑侦探小说,与叙述华丽的散文;大段人物描写与修辞手法是无法在书中找到的。但加缪的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继续读下去。
书中,里厄医生的伙伴嗅了嗅手术室中刺鼻的消毒水,抱怨着:“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仅此而已。”书外的我仔细思索着这个问题,同时好奇里厄医生在彼时彼刻的答案。我想,里厄医生在听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正在进行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手术吧。我想,他应该30岁左右,身形挺拔,清晰的面部轮廓棱角分明吧。我想,他会在病床旁抬起头,用口罩下干涩的双唇告诉他的伙伴:“面对世界的荒诞,世界给了我们三种选择:生理自杀,哲学性自杀和西西弗斯式的反抗。”
我在阅读中抬起头。窗外的北京城睡着了,和奥兰城的夜晚一样寂静。他说得没错,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有人认为,世界的一切的存在都于混沌与偶然中产生,没有任何目的;人们除了存在以外,什么意义都没有。于是,当生命的痕迹开始刻画在时间长流中时,就给了我们几种选择。有人在现实面前选择逃避,于是他们或在悬梁之上自我宣布脑死亡,不假思索地接受所有;或将一切都交予看不见的神明回答----这分别为自杀与哲学性自杀。而在摒弃了逃避后,人们只能选择与现实的荒诞共存。
“西西弗斯式反抗”---名为“Sisyphus”的神明,希腊神话,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故事了。聪明的Sisyphus触怒了众神,于是被惩罚无休止地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每当到了山顶,巨石又会落下,工作便重新开始。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无意义的工作,没有死亡,也没有终点。
“没有比无用与无望的劳动更可怕的惩罚了”。这样一个荒诞冰冷的世界,足以让人绝望窒息。但西西弗斯没有妥协,他在铁律般的禁锢下并没有停滞不前。或许众神正在地狱的另一极--天堂--远远观望,欣赏着这位囚徒苦不堪言的面色与汗流浃背的胴体。西西弗斯在地狱的这一端,在烈日的炙烤下,感受着脚底炎热山石的灼烧,体味着肩头巨石的重量。但在他迈向山顶的每一步之间,都充斥着反叛者的不羁与悲壮;因为他从没有说过向规则妥协,也从未停下过迈向山顶的脚步。连一众神明都不会知道,在表面的痛苦之下,粉饰着的也许是一颗早已决意的内心;名为西西弗斯的英雄,沸腾一般地、无声地嘶吼着,这是他向现实宣告,自己不会妥协。
我后来才读到,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世界观中,认为自杀并非荒诞的结局。荒诞的结局可以是“revolt,freedomandpassion”:所谓passion,是对于“活着”的激情,相信可以用生命的时间来取代生命的质量,活得越多越好。所谓freedom,是超于荒诞的自由,当周围束缚我们的世俗观念破碎时,真正的自我便能得到释放。而所谓revolt,是在接受了人生的荒诞感之后,仍然决心要好好过日子,并希望用自身努力改变建立于荒诞之上的事情。其中,Sisyphus’rebellion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合上书页,目光虽然从书本上移开,心绪却久久徘徊于奥兰城的夜色上空。呼…我险些掉入了哲学自杀的深渊啊。
自杀并不是世界荒诞的必然结局。有多少人因为囿于无力解决现状而选择结束生命、蒙蔽思考的怪圈中;存在主义哲学的诞生,恰巧化解了这一思想困顿。“Therevoltofthefleshistheabsurd.”
我忽然想起,之前的阅读被打断了,书的前言还没读完。于是我又翻回第一页,掠过一行一行的文字,最终在前言的最后一行停下。前言是在年写的,那时候非典正在肆虐,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最后一行说:“最可怕的不是非典,而是非典之后人们的生活仍旧照常。”是啊,面对生命中那些不可磨灭、不可躲避的刻痕,如果在遇见它的存在后仍旧无所作为,混沌度日,这才是最可怕的“自杀”吧。
生命在我的身体上刻下伤痕累累,我会去舔舐它们,抚平伤口;这些还不够,还要敷上药膏,慢慢地绘上新的花纹。从此之后,我选择反抗,向这荒诞的当下,也向往后仍然未知的岁月。
《在舞台中央》
高二16班杭可馨
“你是光,在窗前,投下金色斜方,打亮我的脸庞,带走心里那一点惆怅清凉……”我旋转到舞台中央,带着同伴们跳起手语舞蹈。在歌声中,我们转身、谢幕。灯光渐渐褪去,我仿佛又回到了幕布之后的那段时光……
二年级时,我拎着一双舞鞋,走进了舞蹈教室。这是我母亲鼓励我来的,我先天不协调,母亲说练舞蹈能锻炼我的协调性。第一次课上,我总是手忙脚乱,只能每次偷瞄着前排的同伴,尽力模仿。下课后,我第一个准备溜出教室,但身后传来老师严肃的声音,“hkx,你怎么总是慢半拍,你留下来单独跳一遍。”于是,空荡荡的教室,只剩下我一个学生。两个老师坐在高高的木台上,四只眼睛审视着我。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闻到了绿色地胶的味道,听到了外面的喧闹声,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脸涨得通红,眼泪落在地上。母亲来接我时,舞蹈老师对她说:“这孩子跳不了舞,让她退团吧。”我假装去踩地上的落叶,想象我也能像同伴一样,站在舞台中央,跳出美妙的舞姿——可我只是一个动作僵硬的“小木偶”。
但在母亲和老师的沟通下,我还是留在了舞蹈团。每周三次的集体训练,外加小课,我加倍练习,逐渐跟上了节奏,在表演中也有了一席之地。但我仍时常感到不平,为什么同伴们都能快速地掌握动作,而我却要花费成倍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我们要去参加一场特殊的演出——与两位听力障碍的大姐姐一起为残疾儿童公益演出。排练结束后,老师让我担任一个特殊的位置——在台下做动作,做舞蹈的音乐指挥。演出那天,我在幕后一遍遍摆着动作,合音乐,生怕“慢半拍”会影响到听障姐姐的发挥。这时,我的肩上感到轻轻地一拍,转过头去,是一个听障姐姐。她用不标准的口语对我说,她愿意陪我一起练。练习的时候,她竟也能合上音乐,每一拍都合得那么准;她轻轻地闭上眼,仿佛已经沉浸在了无声的舞蹈当中。我问她练习了多长时间,她竖起手指,比了一个1。一周?一个月?一年!(而我们只用了一个月排练这支舞蹈)她看着我惊讶的表情笑了。
演出时,我在台下做着“指挥”的动作,看着淡蓝色灯光下、白雾之中的听障姐姐们。她们穿着白纱裙,在舞台中央,与我们一起用手语舞蹈,伴随着音乐“……你是风,从林间,穿来淡淡花香,唤醒我的耳朵,吹散心中那一个长影慌张……”当灯光打在她们的脸上,一切都随着她们的微笑柔和起来;她们任由身体在无声中自由舞蹈,云雾也随着她们的裙摆舞动起来。我深深地为之打动。
从那以后,我抹去了脸上常挂的泪水,像听障姐姐一样笑着练习。我尝试真正感受舞蹈,感受身体自然流动,感受空气滑过面颊。每一次练习,我都在表演,在心中的舞台中央。
又一次公益演出到来了,我已成为舞蹈团的主力。在谢幕手语舞蹈的排练过程中,我身旁站着一个智力障碍的小孩。她有着一张圆圆的脸庞,剪着整齐的头帘,眼睛比其他小孩更加明亮纯洁。在我们练习的时候,她只是站着,出神地看着前方。出于学姐的本能,我开始教她动作,给她摆好每一个姿势,鼓励她自己尝试模仿我。
谢幕之际,灯光渐亮,熟悉的音乐渐渐响起“……你是屋檐,在雨中,遮蔽温暖心房,把太阳披在我身上,说那雨是天上风铃叮叮当当……”我与小孩一起站在舞台中央,她用双臂拥抱前方,眼中泛起一种纯真的快乐。我们同台共舞,灯光照亮了我们的衣裙;我们,从黑暗走出,点亮彼此的笑靥、点亮彼此的心灵。
策划
高二年级语文组
海报
钟爱
编辑
姜家源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