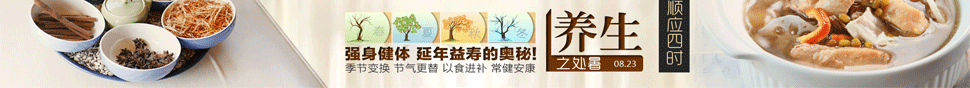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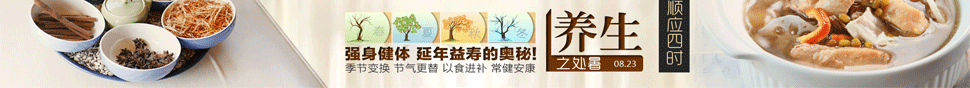
硬皮病是以局限性或弥漫性皮肤及内脏器官结缔组织纤维化或硬化,最后发生萎缩为特点的疾病。本病类似于中医文献中的“皮痹”“肌痹”“血痹”等。“皮痹”最早见于《素问·痹论》:“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赵炳南先生称本病为“皮痹疽”。
一、疾病概述
本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范畴,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在发病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参与,可能与遗传因素、感染因素、血管异常、免疫异常等有关。本病可合并红斑狼疮、皮肌炎、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中存在多种自身抗体,同时细胞免疫也参与了本病的发病过程。血管内皮细胞的损害和功能失调是导致本病血管变化的中心环节。由于血管舒缩功能障碍、小血管结构异常,动脉内膜增殖等变化也是引起本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临床上常分为局限性和系统性。两类硬皮病有不同的临床表现,由于内脏损害不同而预后不同。两类硬皮病均以女性发病率较高,与男性患者相比为3∶1。发病年龄局限性者多数在11~40岁,系统性者在21~50岁。
古籍对本病的记载颇多,如《素问·痹论》所载“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指出其病性为寒。关于病因病机,多责之于内有血气虚或肺气衰,外受风﹑寒﹑湿三气侵袭所致。隋代《诸病源候论》曰:“由血气虚则受风湿而成此病日久不愈,入于经络,搏于阳经,亦变全身手足不随。”明代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曰:“五痹之生,不外于风寒湿之气也……肺气衰则三气入皮,故名之曰皮痹。”宋代吴彦夔《传信适用方》记述:“人发寒热不止,经数日后四肢坚如石,以物击之似钟磬,日渐瘦恶。治以茱萸、木香等煎汤……”由此可见,历代医家详细论述了其病性病位、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
张志礼认为本病多因营血不足,外受寒邪,血行不畅,凝于肌肤;或因肺、脾、肾阳气不足,卫外不固,腠理不密,风寒湿之邪乘隙侵袭,阻于皮肤肌肉之间,伤于血分,致荣卫行涩,营卫不和,气血凝滞,经络失疏,血脉阻隔,气血凝滞而发病。
二、辨证论治
(一)脾肾不足证
[主证]皮损多为局限性硬皮病,初期为躯干或四肢水肿性红色斑块,皮损呈斑块状或条索状,皮纹消失,表面光滑如涂蜡,局部可见变硬,萎缩,呈板样,触之质硬,表面可出现色素加深或色素脱失,或呈黄色,或呈褐色,周围可见紫红色晕。舌质淡,舌边有齿痕,苔薄白,脉沉缓或迟。
[辨证]脾肾不足,兼感寒邪,气血凝滞。
[治法]健脾益肾,温经通络,活血软坚。
[处方]黄芪15g白术10g茯苓15g山药15g
党参10g当归10g白芍10g桂枝10g
丹参15g鸡血藤30g红花10g白芥子10g
鬼箭羽30g夏枯草15g僵蚕10g木香10g
(二)肺脾肾俱虚证
[主证]初起皮损为实质性水肿,以后萎缩、变硬,自觉乏力倦怠,畏寒明显、四肢末梢发凉,关节疼痛,甚至活动受限,口干舌燥,食欲差或腹胀、腹泻。可出现面部表情僵硬,鼻尖变小,口唇变薄,吞咽困难。妇女常有月经滞涩或停经现象。舌质淡,体胖嫩或边有齿痕,脉沉伏或沉紧。
[辨证]肾阳虚损,脾肺两虚,气不化水,寒凝血滞。
[治法]健脾肺益肾,温阳化水,活血软坚。
[处方]附片6g(先煎)肉桂10g生黄芪30g党参15g
白术10g茯苓15g僵蚕10g当归10g
鸡血藤30g熟地10g仙灵脾10g杜仲10g
白芥子15g麻黄6g鹿角胶15g(烊化)车前子15g(包煎)
随证加减:以上两证,伴有咳嗽气喘者,加麻黄、苦杏仁;伴有咳嗽痰多者,加桑白皮、地骨皮、百部、鱼腥草;伴有纳呆、腹胀者,加炒薏苡仁、白扁豆、枳壳、陈皮;伴有关节疼痛者,加羌活、独活、伸筋草、丝瓜络、路路通;肾阳虚者,加菟丝子、仙茅、仙灵脾、附片、肉桂、鹿角胶;肾阴虚者,加女贞子、墨旱莲;气虚者,加太子参、人参等。
三、临证经验
张志礼认为本病以寒证居多,患者肢冷肤寒,遇寒加重,舌淡苔白润,均为寒性特点。发病早期,皮肤表现为发热,或紫红,触之而热,多为外邪侵袭,以实证或本虚标实多见。中后期脏腑气血不足,以虚实夹杂证及虚证多见。病位虽在皮肤,但与肌肉、筋骨、关节及肺脾肾脏腑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辨治时需详辨寒热、虚实。皮痹初起时,以祛邪为主;虚实夹杂证,则祛邪与扶正兼施;日久损及正气,则以补益气血,补益肺气,温补脾肾为主。
本病呈慢性病程,以肺虚、气虚、血虚,特别是脾肾阳虚最为常见,以皮肤萎缩、肌肉削瘦、肢冷不温等临床表现为辨证要点。张志礼谨守脾肾阳虚、气血凝滞为本的核心病机,若脾运失职,水湿停滞,则肌肉失养,卫外不固,腠理不密,则易感外邪而得病;肾藏精,主命门火,能温煦和推动各脏腑的功能活动,防卫外邪侵袭,肾阳虚衰,则形寒肢冷、消瘦乏力、腰膝酸软、齿摇发落,这些症状常见于硬皮病。而皮肤发硬,关节酸痛,张口伸舌困难,肢端青紫,月经不调或停滞等,均为气滞血瘀之征。故以健脾益肾,活血化瘀,散寒通滞为法贯穿始终。处方常选用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理中丸、阳和汤、金匮肾气丸、真武汤、黄芪桂枝五物汤、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泻白散和麻杏石甘汤等方药加减。
中成药治疗方面,常辨证选用人参健脾丸、人参归脾丸、大黄?虫丸、活血消炎丸、阳和丸、软皮丸、当归丸、黄精丸、八珍益母丸等,用以后期巩固治疗。
外治时,可应用中药熏洗浸泡,同时配合正红花油局部按摩应用,还可配合拔膏疗法温化贴敷,以软化晚期皮损。常用的中药熏洗方:伸筋草30g、透骨草30g、蕲艾15g、制乳没各6g,煎水热洗。
四、典型病案
刘某,女,44岁。年3月2日初诊。
患者3个月前受凉后自觉低热乏力,食纳减退,轻咳少量稀薄白痰,胸闷气短,全身不适,继之手足发凉,关节肿痛,近3周面、胸、背出现大片同皮色的水肿性斑块。皮科检查:体温38.1℃,面、胸、背可见大片不规则型水肿性硬斑,表面坚实发亮,压之无凹陷,双手背发紧肿胀,握拳困难,触之稍硬。舌淡体胖,苔薄白,脉细。
[中医诊断]皮痹。
[西医诊断]系统性硬皮病。
[辨证]肺脾两虚,兼感风寒湿邪,气血凝滞。
[治法]宣肺健脾,利水消肿,活血软坚。
[处方]麻黄3g杏仁10g炙甘草10g生黄芪30g
白术10g茯苓15g桑白皮15g冬瓜皮15g
泽泻15g桂枝10g白芥子15g车前子15g(包煎)
秦艽30g丹参15g鸡血藤30g
外用药:伸筋草30g、透骨草30g、蕲艾15g、乳香6g、没药6g,煎水外洗。每日1次。
[二诊]服上方14剂后胸闷气短明显减轻,关节疼痛大减,躯干及面部肿胀斑块明显消退,上方去杏仁、炙甘草、冬瓜皮,加红花15g、刘寄奴15g、夏枯草15g、赤芍15g,继服1个月后症状基本消退,唯手足仍发凉。
[三诊]此后,患者未坚持服中药,年冬因受寒后症状复发,医院给予激素、山莨菪碱及静脉封闭等治疗,症状逐渐加重,消瘦乏力,心悸,气短,畏寒肢冷,关节疼痛,食纳减退,吞咽困难,腹胀便溏,月经滞涩,于年8月16日,又来我院诊治。
诊查:周身皮肤板状坚硬,手足尤甚,皮纹消失,面少表情,鼻尖耳薄,眼睑不合,口唇缩小,舌短难伸,四肢皮损暗褐色,有蜡样光泽,手指皮肤不能捏起皱褶。舌质淡,舌体胖,有齿痕,脉沉。
[辨证]脾肾不足,气血两虚,经络阻隔,血脉瘀滞。
[治法]健脾益肾,养血益气,温经通络,活血软坚。
[处方]黄芪30g白术10g茯苓15g党参15g
木香10g枳壳10g薏苡仁30g桂枝10g
白芥子15g僵蚕10g丹参30g红花10g
鸡血藤30g赤芍15g当归10g秦艽30g
白人参10g(另煎)
外用药:使用正红花油按摩局部至温热感。
[四诊]服上方14剂后,精神食纳好转,关节疼痛减轻,腹胀稍缓解,大便正常,局部皮损稍变软。上方去枳壳、薏苡仁、白人参,加鹿角胶10g(烊化)、女贞子30g、附片10g、肉桂3g。
[五诊]服上方30剂后,症状大减,张口较前大,吞咽已无困难,有时局部微微出汗,皮损仍硬,月经来潮、量少色淡。
此后,随证加减,曾用过女贞子、山茱萸、仙灵脾、首乌藤、伸筋草、丝瓜络、鬼箭羽等,共服药3个月,全身情况明显好转,精神食纳正常,局部皮损明显变软,外观已接近正常,继以阳和丸、人参归脾丸调理,随访1年无复发。
[按语]本例患者发病初起因素体虚弱,风寒湿邪侵袭,累及脏腑,出现肺卫不宣,邪郁化热,经络痹阻症状,故用麻黄、杏仁、桑白皮以宣肺利水开鬼门,益气消肿(麻黄、杏仁宣肺平喘;麻黄还可助桂枝、白芥子宣肺散寒利水);黄芪、白术、茯苓健脾益气;茯苓又助桑白皮、冬瓜皮、车前子、泽泻等利水消肿;辅以丹参、鸡血藤、秦艽活血化瘀通络,故症状显效。可惜患者不愿长期服中药,以致病情迁延。3年后患者病情已经进展至硬化萎缩期,出现食管、心、肺之硬化症状,此时辨证为脾肾不足,气血两虚,经络阻隔,血脉瘀滞。但患者食少纳差、腹胀、便溏等脾虚症状突出,故张志礼首先从健脾益气入手。予白人参大补元气;黄芪补中益气,升阳固表,合党参补脾肺之气;白术、茯苓益气助运,健脾渗湿;以桂枝散风寒而温经通痹,与黄芪合用,益气温阳,和血通经;当归、赤芍、丹参、鸡血藤、红花养血活血,化瘀通络;生薏苡仁、白芥子祛寒痰湿滞;木香、枳壳行气消滞;僵蚕散风活络、祛痰散结。待患者脾虚症状缓解,精神食纳好转后,进而用鹿角胶、附片、女贞子、仙灵脾等温肾壮阳,温经散寒,从而使3年迁延加重的顽症经治疗3个月后,病情显著改善。
本文节选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年10月出版的《精诚大医张志礼》,主编:
王萍,张芃,娄卫海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